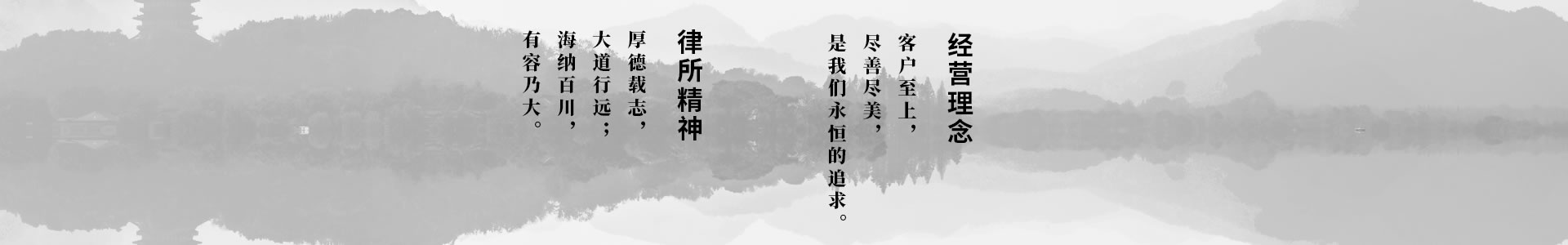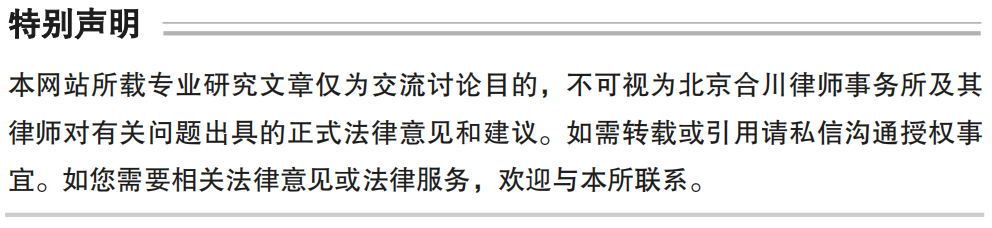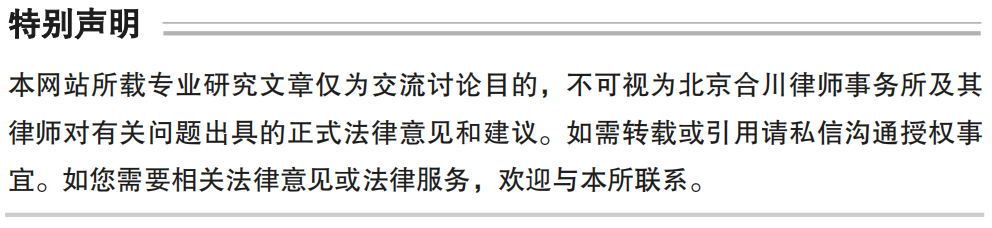朱崇坤 赵文雅:诉讼中“新证据”与“新事实”的界定……
—— 诉讼中“新证据”与“新事实”的界定与司法实践启示
在笔者承办的一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再审案件中,核心争议是当事人收到二审判决后,公司破产管理人在另案中形成的一份关于股权转让价款是否付清及公司整体利润的审计报告是否构成再审新证据。该案经历听证审理,再审法院以该审计报告系“单方委托”以及“不符合客观原因不能提交”否定其新证据效力。这一认定反映出司法实践中对新证据审查标准的僵化适用,也引发对于新证据认定标准及实务策略的深入探讨。
新证据的认定需符合客观性障碍、关联性及时间性三项要件【1】。在(2018)最高法民申5968号中,最高院认为“再审新证据,其实质要件应为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形式要件则是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的证据,或者即便证据是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但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而在本案中,新的审计报告形成于破产程序中,原二审判决之后,表面上似乎与原审阶段无直接联系,但其证据资格应从多个角度进行论证。
首先,破产程序的强制性和排他性决定了原审期间当事人客观上难以获取破产相关财务数据,而公司账簿、印章均由管理人掌控,这种情况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86条所述的“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发现”的情形。因此,破产程序的后置带来的程序阻碍应被认定为客观障碍,而不能简单归咎于当事人举证懈怠。
其次,破产管理人作为法院指定的中立机构,其委托审计行为系履行《企业破产法》规定的职责,审计结论具备一定的公文书证属性。与普通当事人单方委托的鉴定结论相比,破产审计报告的司法辅助性质决定了其证据资格的特殊性。司法实践中,不乏将破产管理人审计报告作为有效证据采纳的案例,再审法院对于“单方性”的认定存在瑕疵。且从证据实质内容角度分析,该审计报告揭示了股权转让款的超额支付情况,且公司所有者权益为负。这一事实直接推翻了原审法院对核心争议问题的认定。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法院在审查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是否属于“新证据”时,容易混淆新证据与新事实的概念。新证据是指对原审已经存在的事实提供新的证明方法,例如本案中的破产审计报告对付款事实的重新审计;而新事实则是指原审结束后发生或发现的全新事实,相较于新证据的补充功能,新事实具有“重构案件基础”的效力,其本质是原审结束后新发生或新发现的法律事实,且该事实足以动摇原裁判的根基。在本案中,审计报告虽然形成于原审之后,但其内容是对原审争议事实的再次认定,因而应认定为新证据而非新事实。
从律师实务角度看,办理类似案件时,可首先明确证据的法律性质,区分公文书证与私文书证,并利用破产程序的特殊性削弱对方“单方委托”抗辩。其次,围绕客观障碍进行举证,通过提交破产受理裁定、管理人履职报告等材料,构建完整的时间线证明证据提交的合理性。本案反映出新证据认定中保守主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律师在再审阶段的工作,不仅是对证据规则的应用,更是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平衡的探讨。
【1】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列证据可认定为“新的证据”:
(1)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证据。
(2)虽然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
(3)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但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证据。
(4)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已经提供,原审人民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的证据(原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不予采纳的除外)。
需要注意的是,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的证据能否作为“新证据”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看能否依据该证据另行提起诉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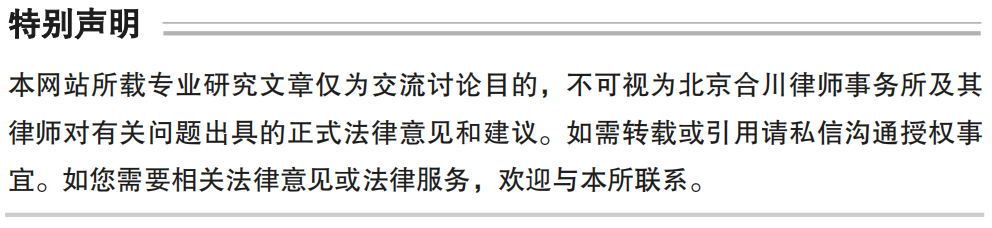

上一篇:朱崇坤:公司法定代表人涤除困境与解决路径探究
下一篇:最后一页